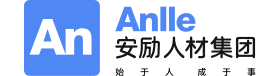最近,张维迎与林毅夫两位经济学家的“产业政策之争”可谓“一石激起千层浪”,随后,很多学者围绕着要不要产业政策,怎么用产业政策等一系列问题展开了广泛讨论。在笔者看来,这其中,更深层、更核心的问题或许还不在“产业政策”本身,而在于其背后所反映的思维方式。
首先,“产业”是一个局部均衡意义上的整体性概念,它意味着把相同或类似的产品归为一类。任何一个社会中,必然都有很多不同类型的商品,如家电、服装、汽车等等,于是,人们根据这些不同类型的产品划分出不同类型的产业。“产业”这一概念的出现为人们考察经济问题带来了便利,但同时也产生了很大的副作用,以致很多人容易像林毅夫教授一样,忽视产业背后的“个体”因素。众所周知,产业的背后是企业,是企业家的创新,没有企业与企业家的创新,就没有产业与产业的成长。准确地说,当一个或多个企业成长起来时,才切切实实地出现了“产业”,所以,考察产业问题的正确逻辑应该从“企业”(企业家)到“产业”,而林毅夫教授却颠倒了因果,在他看来,要事先认为有发展某个产业的必要,然后出台产业政策激励企业创新,显然,这是一种从“产业”到“企业”的思路。
再有,“产业”的背后是“能力”(知识),只有具备了创新能力,才能把一个产业支撑起来,同时,只有不断的创新才能使一个产业持续存在与发展,而这样的能力是隐藏在企业组织中,隐藏在企业家的头脑中的,政府不可能人为地创造出这样的能力。根据许小年教授提供的资料,沃顿商学院专门研究创新的教授认为,有关创新动力的来源,他们只能解释5%,其余95%无法解释,既然商学院的教授都不明了创新的来源,那么政府更难能知道。
不仅如此,“产业政策”的思维还体现在经济学家把其个人的价值判断“普遍化”为他人的价值判断。但实际上,在市场经济中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判断,个体根据自己的价值判断,把资源配置到他认为最有利于改善他处境的方面,但“产业政策”隐含的却是个体要服从某个经济学家的价值判断。换言之,经济学家已经替他做出了最有利于他的价值判断,因此,其言外之意就是把个体配置资源的权利交给经济学家,听从经济学家的指挥来配置资源。
显然,林毅夫教授不是从个体(的价值判断)的角度思考问题的,在他看来,某个他认为有必要发展的产业若发展起来了,就算是“大功告成”了。殊不知,“成功”是个体的、主观的概念,一个个体,只有当他实现了其自身的目标时,他才有可能认为自己是成功的。那么,产业的成功怎么可能代表个体所认为的成功呢?因此,政策的目标应着眼于为每个个体的成功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,而不是无视个体,甚至把个体作为实现某些经济学家所认为“成功”的手段。同时,经济学所研究的基本问题,也一定不是关于如何实现某个产业的发展,而是如何使无数的个体更好地实现他们自己的目标,更好地自我实现,也即,经济学是关于“价值”、关于“意义”的,而不是关于“产出”、关于“数量”的,而产业政策只关注“产出”的数量,忽视了“价值”的意义。
此外,“产业政策”的这种思维还体现在对逻辑方法的误用上。当我们说“逻辑”时,是指个体在行动时总是离不开逻辑的,他要达到自己的目标,必须应用他认为正确的因果关系,这样他才能行动。实际上,个体的任何行动总是受他接受了的因果关系所支配,尽管他所接受的因果关系有时是错的,这导致他不能如愿以偿地实现自己的目标,但个体也会从“经验”中学习,获取有助于实现与自己目标相关的知识。但问题是,林毅夫教授的逻辑不是从个体出发,而是根据自己对发达国家的考察或实证研究,由此,在“资源禀赋”与“产业”等“现象”之间建立了他所认为的因果关系。然而,由于任何现象都是人们行动的产物,而人们的行为又是观念的产物,当观念改变时,现象也就随之改变了,所以,“现象”之间不存在确切的因果关系。
最后,需要强调的是,这种思维方式也意味着个体放弃其自身的价值判断和独立思考,一切以流行的观念为准绳。比如,认为获得国家基金就是水平高的,发表在“权威”刊物上的论文就是好的,以及基础设施就应该由政府来投资等等。但实际上,无论是制度创新还是技术创新,都要以个体的独立判断与独立思考为前提。